

我是棠棣,一枚歷史愛好者。歡迎大家【關注】我,一起談古論今,縱論天下大勢。君子一世,為學、交友而已!
1853年,太平軍攻克江寧府城之后,向榮率部從小丹陽繞道秣陵關,進扎天京城東二十里之沙子岡。
4月5日,清軍逼近孝陵衛,與鐘山太平軍接仗。向榮駐營后,4月7日,全面進攻鐘山,遭到太平軍猛烈抵抗,傷亡近二百人,只得暫扎孝陵衛,武裝監視天京,時稱江南大營。

所轄兵勇32615人。
其中:
在天京戰區應為27435人(抵達大營僅有17800人),留守湖南3300人,湖北1880人。
向榮為欽差大臣,大營統帥,內閣學士許乃釗幫辦軍務,按察使彭玉雯總辦糧台事務。軍餉由湖南、廣西、廣東三省負擔,補給線遙遠,轉運艱難,餉需供應時有中斷。
向榮只得請江西巡撫張芾籌濟,江蘇也墊撥白銀二十萬兩,句容縣提供漕米三萬余石,緩解了燃眉之急。大營又在皖南太平府暫設轉運局,委前河督潘錫恩主持其事。
太平軍攻占鎮、揚后,向榮只令總兵李瑞統軍二千人馳援常州,防堵太平軍進攻蘇南。
向榮堅持集中主力進犯天京,可是,楊秀清令鐘山將士固守營壘,殺傷敵軍,挫敗了向榮連次進犯。于是,首都東郊呈現相持戰局。
是時,欽差大臣琦善令幫辦軍務陳金綬、四品京堂勝保率前隊循長江北岸東進,3月30日,抵江浦,4月4日,攻陷浦口。中旬,清軍趨揚州,在城北駐屯,時稱江北大營。
清廷共征調二萬四千名兵勇,到達前線旗綠兵丁不過萬人,實力與素質皆遜于江南大營。
琦善主持大營,清廷又擢勝保幫辦軍務,還詔署四川總督慧成馳赴揚州。大營承擔浦口到揚州間漫長戰線的防堵任務,兵力嚴重不足。
琦善消極遷延,「不欲急攻」,不愿把太平軍引向北岸。勝保抵制,并連續進攻獲勝,琦善拒絕接應,致使攻勢不能持久與擴展。
面對清軍集結,春官丞相胡以晃赴揚州,與林鳳祥、李開芳籌措防御。他們蔑視琦善,「拍掌大笑,登城吹唱」,并在城外構筑土城、工事,加強軍事地位。
由于琦善緩攻不戰,雙方都缺乏積極意圖,揚州前線也成相持戰局。
琦善集中兵力于揚州,住在城北二十余里的袁姓花園,「終日取樂」,揚州西南「濱臨運河,絕無一將一兵」。太平軍「終日大開南門,出入自由」,與寧、鎮互為犄援。

琦善傳令各營, 「間日用炮轟城,炮遠不能及城」,以敷衍陳奏,蒙蔽咸豐。至于沿江防御,他一概不管不問,惟奏請「迅速添派北路綠營官兵」前往防堵。
清廷則無兵派遣,防堵徒托空言。
因此,揚州戰局更加消沉。
4月下半月,楊秀清決定分兵北伐與西征,遂開始收縮天京防線。18日,太平軍棄守七橋甕據點。20日夜,燒毀鐘山營盤。
于是,東郊險要陷于敵手。向榮迅調兵勇二千四百人進犯雨花台,妄圖圍困天京。同時,他又遣鄭魁士專程馳赴江陰,向楊文定提取戰船,還降謫李瑞職務,改派江南提督鄧紹良指揮鎮江軍事,另辟東戰場。
至此,清軍在三城外圍分別構筑弧形封鎖線,施加一定的軍事壓力,影響與制約著太平天國的戰略決策。當時,清廷還糾集第二線兵力,重在黃河河防,企圖防堵太平軍北伐。
必須指出,清軍總兵力當在十萬以上,前線為三萬五千人。分布地區廣闊,相互缺乏配合援應,機動能力較差,顯然難以堵截太平軍在其內線的運動與發展。
太平軍能征將士約為十萬,集中部署于三城及江面,與清軍兩大營實力相比,居于優勢。
尤其是強大的水師控制長江航道,增強了機動力。按理說,太平軍應當發揮優勢,各個殲滅兩大營敵軍,挺進蘇南、浙江,開辟江南版圖,走朱元璋之路。
但洪、楊計不出此,卻實施防御三城,分兵運動的戰略決策,以致錯過時機,分散兵力,鑄成嚴重的戰略失誤。
1853年4月底,太平軍完成分兵運動的準備。天京城外營壘大部焚棄,「惟于各城門口外,深溝高壘」,同時,在下關東西加筑土城,強化水營防衛。
揚州將士也自城外撤防城垣,并調林鳳樣、李開芳就任北伐軍統帥,抽撥揚州、天京部分將士,組成北伐兵團,鎮江、天京部分將士組成西征兵團,以賴漢英為統帥。
兩兵團避實擊慮,分別向中原及江西展開戰略運動,在清軍后方開辟戰場。

分兵之后,太平軍極力防守三城,北王韋昌輝指揮保衛天京,羅大綱駐守鎮江,曾立昌駐防揚州。
太平軍具有高超的城市防御戰術經驗,三城垣高池深,濱臨江河,城外有險可恃,更加強了防御者的軍事地位。
先看天京城防體系。
太平軍在各城門外據險筑壘,雨花台營壘最大,廟宇、僧房皆經改造而成堅壘。山頂筑望樓一座,與報恩寺并峙,監視敵人動向,指揮南線各營將士進退。城外街道也駐兵設防,聯結城軍與雨花台守軍,「互為援應」,構成南線防御縱深。
其他各門城垣,「東南高至六丈,西北亦至四丈以外。」城北為后湖,寬約十余里,無可問渡。東西南三面均系秦淮河水環繞,寬自四五丈及十余丈不等,橋梁早被拆毀。只有東北一隅陸路可以進兵。
但太平軍「已筑柵挖濠數道,并力拒守。」
東郊自紫金山至龍脖子,太平軍深濠重塹,遍置竹簽茨藜,「以營護城,復以城護營,防守極其嚴密。」
韋昌輝非常重視城防體系的正面,以為防御重點,使向榮望而生畏。
與正面防線相比,其他方向防務薄弱,雖「深溝固壘,虛插偽旗」,但兵力不多。「所恃者營內望樓、營外濠溝、營門口槍炮。」營盤兩翼不配置兵力,只遣小隊設置潛伏哨,「伏路守夜」。城上駐守將士,「隔數垛放一槍炮,設一望樓」,擊鼓報更。
垛口之間儲備火藥包,巡查分隊日夜分段檢查防務,嚴杜疏漏。

天京江防是城防體系中的重要環節。
水營設在下關,指揮唐正財建館大王廟側,主持水師。
下關沿江建筑磚木結構的城墻,開有槍炮眼孔,墻內設望樓多座,監視江面。
在水府祠江口外構筑木城,遮掩江口。其后安設十余門重炮,封鎖江道。并且駐泊炮船,護衛水營,沿江設立三道水關:「中關設于儀鳳門外鮮魚巷口河下,頭關設于上河夾江,下關設于七里州河內。」
三關「各有營盤圍護,每關設望樓一座」,瞭望來往船只。各水營配有炮船,灣泊木城內,以備游弋巡查。水師不僅承擔保衛首都江防,而且要為沿江戰場提供船只、水手,運輸糧食軍資,接濟三城將士。
韋昌輝坐鎮北王府,通過城內外的望樓系統掌握敵情,指揮戰爭。城外各營、城頭及城中皆設望樓,「大街小巷無處不有」。
望樓高約五丈,共三層,可以相互連絡,「輪班擊鼓以報更次。」發現敵情時,立即揮動不同顏色的旗幟,依次向北王府紅更樓報警,說明敵軍進攻方向、聲勢。同時,吹螺擊鼓,傳遞信息,速度極快。其中,雞鳴山三座望樓尤其重要,密切監視正面敵軍,為北王提供準確信息,及時作出判斷和決策,調集機動兵力投入關鍵戰場,遏制清軍攻勢。
向榮本來就感到兵力不足,現在因太平軍分兵運動,被迫遣兵勇馳赴鎮江、東壩、江西、揚州等地竟至萬人,進犯天京兵勇僅一萬四千七百人,從紫金山至七橋甕扎營十九座,綿延十二三里,構成正面戰線。其余七十余里城垣,「皆為兵力之所不到。」
況且,缺乏水師,無力與太平軍在江面爭鋒。向榮只得維持消極相持的戰局。
羅大綱與吳如孝分駐鎮江、瓜洲,控扼京口江面,水陸保衛下游重鎮。太平軍「拆南門外虎踞橋,開西門」,由農村獲取糧食補給。

并鑿通「府治后垣,緣龍埂筑堞至北固山頂。又自山西沿江筑城,西至江口,包瓦子山,循運河而南」,綿亙六里,筑六座炮壘,構成西北防線。南北江面駐泊師船數千只,連結瓜鎮,維系軍資供應。
羅大綱針對清軍紀律敗壞,燒殺淫掠,激起群眾強烈義憤,嚴申太平軍紀律,強調「一切買物給價公平」,有力爭取了民心,為反圍剿斗爭創造了有利的群眾條件。
揚州防御最為薄弱。5月8日,胡以晃、林鳳祥等率主力撤出府城后,精銳將士「不足千人」,余皆新兵。曾立昌決定收縮防線,撤出灣頭等城外據點,焚毀了城周十余里的民房,將士撤入城內,恃城負固。琦善乘機推進,逼城扎營,構成新的封鎖線。
清軍大致分布態勢是:
琦善、陳金綬分營雷塘集、堡城及司徒廟,勝保略地至五台山,查文經以滁州勇屯灣頭、陳家巷、萬福橋、長春營、沙岡。
包圍圈收縮,但圍而緩攻戰略方針不變。急于事功的勝保不能忍受,憤而疏劾琦善牽制消極,致使他「孤立難成」。他指控統帥「少能容物」,改竄奏折, 「極力鋪張」,戰略決策「但求自立腳步,不計實功」,而且疑忌下屬。
因此,揚州戰局遷延日久,「屢失機會,實為可惜」。咸豐一再嚴旨追責,琦善我行我素,使曾立昌得以堅守城垣,并與瓜鎮及天京聯絡,保持對峙局面。
可是,與天京相比,揚州無疑成為清軍注目的薄弱部位,以致首先淪喪。
1853年5月上旬,太平軍分兵運動,向榮以為有機可乘,連續向雨花台西路發動攻勢,皆被太平軍挫敗,「一時驟難得手。」

只得改變進攻重點,增兵進犯鎮江,妄圖取得突破。為此,鎮江清軍增至八千人,鄧紹良進抵距城十里之甘棠橋扎駐,和春則指揮水師駛泊丹徒江面,配合陸師進犯。
羅大綱決定先發制人。5月7日,率軍至觀音山誘敵,以主力由釜鼎山迂回敵后,消滅清軍三百余人,迫使鄧紹良不敢輕舉安動。9日,太平軍水陸迎戰,勇挫和春從水路進犯鎮瓜的冒險行動。
向榮只得增兵二千,鄧紹良軍勢復振,移營京峴山,距城東五里。羅大綱于5月下旬督師出擊清軍,未獲勝捷,遂轉拒守,「彌月不敢出。」
6月30日四更,他又以火船焚燒清軍艇船,亦因被察覺防范,而功敗垂成。
7月中旬,鎮江清軍被抽調一千二百人援贛,兵力削弱。而且,鄧紹良縱兵掠民,兵勇強占民房為營,引起民憤沸騰,紛紛投奔太平軍。
羅大綱趁此晝夜進攻,清軍在酷暑烈日之下緊張抵抗,疲憊不堪,難以再戰。18日正午,太平軍出城誘敵,與清軍在城下相持。羅大綱令北固山將士切斷清軍后路,迫使鄧紹良分兵相持。
羅大綱立遣精銳在城垣開暗門潛出, 「直撲大營,火箭、火罐等物一齊拋放」,清軍巢穴起火。鄧紹良旋即敗潰丹陽,環城七營皆被焚毀。
21日,太平軍進據丹徒,鎮江戰局出現轉折。
向榮疏劾鄧紹良革職留用,調回紫金山大營,改派和春主持鎮江軍務。22日,和春抵馬陵、辛豐一線,防堵太平軍進軍蘇、常。其實,羅大綱缺乏力量發展,8月9日,棄守丹徒、京峴山,被和春乘機盤踞,與甘棠橋南清軍互為犄角,鎮江前線又恢復相持戰局。至此,向榮「先復鎮江」的計劃宣告破滅。
是時,上海小刀會起義,9月間,連克周圍各縣。向榮見餉源受到威脅,立即請署江蘇巡撫許乃釗率大營、鎮江兵勇三千余人馳援上海。這樣,江寧清軍更加削弱,戰局消沉。向榮趁此修改戰略計劃:先取上海,次下鎮江,最后圍攻天京。
天京戰局比鎮江相對沉寂。江南大營分兵四出,成了空架子。而且,軍餉供應困難。截止1853年7月,戶部指撥大營餉銀二百三十八萬兩,實收僅一百四十八萬兩,已支軍餉一百零五萬兩,尚存四十三萬兩,只能維持到8月。
因太平軍西征,向榮被迫把糧台遷往大營。江西餉源已受太平軍威脅,上海又被小刀會占領,大營缺餉更趨嚴重。
向榮雖為欽差大臣,但未身兼督撫,沒有權力在地方自行籌餉。嚴重缺餉限制了江南大營擴軍,而且使現有兵勇因欠餉漸多而消極怠戰,影響了戰局發展。
向榮年過六旬,腿足患疾,不能上陣指揮,「委之參將游擊」,軍令「即不嚴明,保舉各憑愛惡」,加深軍營矛盾,「往往自相仇殺」。

1853年5月,向榮移營紫金山,以楚兵為主力,構成清軍東路集群。江寧將軍蘇布通阿管帶川兵為主力,扎營七橋甕,構成南路集群。
從6月至9月,清軍或者強攻雨花台,或者偷襲神策門、太平門,或者蠶食龍脖子據點,皆未得逞。
韋昌輝實施負固堅守的戰略,與楊秀清的分兵運動的總體戰略正相配合,取得頗大的牽制效益。
戰場主動權操持于楊秀清之手,牽制江南、江北大營于三城,分兵開辟上游基地,建立戰略后方。
石達開于9月奉命主持西征,太平天國戰略重點隨即放置上游。于是,原來分兵運動、牽制兩大營清軍分散兵力的有限戰略目標發生演變,分兵發展成為主要目標,相反,三城防御變成有限的牽制戰場。
西征使天京「接濟無窮」,弄得向榮「陸攻不得,水攻不能,日對堅城,一籌莫展。」
當初吹噓的速戰速決、攻取天京的大話收回了,代之以上海鎮江——南京的攻堅程序。
向榮被迫承認,這是一場持久戰。在這樣的戰略進攻程序里,天京戰場遂成為牽制性的次要戰場。
林鳳祥、李開芳抽調揚州太平軍主力北伐,曾立昌留守府城,兵力銳減。
除了加強城防外,他尤其注重江防,保衛水上接濟線的安全。
太平軍以「鐵索橫諸江,加木馬如笮橋,朝夕馳應」,使揚瓜鎮聯成一體,加強防御地位。琦善見揚州守御力量削弱,于5月下旬加強攻堅,兩次開鑿隧道,轟塌天寧門城垣。曾立昌臨危不懼,率軍堵御,「隨時補筑」,挫敗了攻勢。
慧成也在琦善失利后,進犯東門,旋因南門太平軍出擊后路而慌忙撤軍。
琦善只得回到圍而緩攻的舊轍。揚州太平軍處境日艱,補給線受到威脅,火藥匱乏,牽制了江北大營清軍。當北伐軍長驅中原時,清軍「征調緩不濟急,幾于無兵可調,無款可籌。」
可見,揚州防御戰局有力策應了北伐軍的勝利轉進。
6月18日,勝保率部二千人馳援開封,詔命侍郎雷以諴幫辦軍務。
其時,新任漕督福濟抵達揚州,與雷以諴合作,多次進據虹橋,企圖切斷瓜揚通道。7月20日,曾立昌與瓜洲守將吳如孝夾擊虹橋,大敗清軍,重開揚州陸路補給線。
之后,江南大營悍將、總兵瞿騰龍防堵六合事竣,受琦善指令,與雙來協同攻城。
曾立昌早已防范, 「穴城設炮」,增強火力。7月23日,清軍仰攻,被猛烈炮火擊退,雙來再次中彈,不久殞命。
琦善攻堅慘敗,前驅喪失,乃疏留瞿騰龍,并調整圍困部署:
琦善扎營城北,陳金綬扎營城西,署參將馮景尼扎營城東,總兵多隆武扎營城東北路,東南路由慧成派熱河兵四百名駐扼,西北路蔣王廟駐扎步騎一千人,南路三汊河集結兵勇一千八百人,切斷瓜揚水路交通線。

雷以諴駐營萬福橋,為東北路后援。曾立昌令將士組織突擊隊縋城攻擾,清軍防不勝防, 「多在近城處埋伏,駐營者甚屬寥寥」。后路空虛,琦善「萬分焦灼」。
8月5日,曾立昌向吳如孝求援。瓜洲將士「駛入運河,直抵三汊河」,試圖打通水路補給線。
清軍精銳瞿騰龍、德興阿、毛三元等部投入抵抗,戰斗十分激烈。
其時,曾立昌多次遣隊武裝偵察清軍防線,準備策應援軍。
琦善竭力合圍揚州,嚴堵運河東岸,沉石釘樁封鎖城外河道,陸路要隘設卡駐兵,切斷揚州補給線。他的如意算盤是:
「城中食盡,外援不至,即可……收復郡城。」
其實,琦善根本拿不下揚州,因為江北大營分崩離析,腐敗不堪。大營幕僚、糧台委員乘機搜刮享樂,與江南大營文武爭相比擬。
琦善「老而無志」,行將就木,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。雷以諴貪婪聚斂,無所不用其極。
7月,他接受幕客錢江建議,自籌軍餉,編練壯勇,欲與琦善抗衡。籌餉主要方法是勸捐與抽厘。
勸捐在各軍營早經推行,厘金則是雷、錢獨創。
「其法:于商賈所得利,出入一錢,官取其厘。分別城市大小,居者立局,行者設卡。」
是為行厘與坐厘之分,都屬于商業稅性質,稅率百分之一。「于是軍餉有資,源源而入,取之不竭。」
厘金首先在仙女廟、邵伯、宜陵、張網溝等地開征。之后,各戰場將帥先后推行厘金,成為軍餉的主要來源之一,后被清廷作為一項常稅,直到1931年才被國民黨政府取消。
1853年冬,北伐軍進逼天津,西征軍圍攻廬州。咸豐兵餉俱竭,亟欲揚州首先突破,以抽出機動兵力,次第克服鎮寧。但琦善只想坐收圍困揚州,逼走太平軍之功,并不急于攻堅。咸豐的旨意不得落實,揚州戰局沒有起色。
11月底,楊秀清以賴漢英為統帥,抽調天京及上游將士,組建援揚兵團,駛抵瓜洲,會合瓜鎮將士,扎營數十座,進逼三汊河。

接著,援軍分兩路:
一路牽制三汊河清軍,一路由賴漢英親率由水路進襲儀征,欲攻江北大營側后,以解城圍。
12月2日,太平軍駛抵儀征沙漫洲登陸。3日,乘虛攻克儀征。4日,瓜洲將士萬人進攻三汊河,曾立昌率將士四五千人,分三路殺出南夾攻,但被清軍擊退。
兩軍相持一旬后,賴漢英買通壯勇以為內應,決定由清軍防務薄弱的東路突破。12月24日,太平軍進抵東石、人頭一帶,牽制三汊河清軍。同時,瓜洲將士由運河東岸潛渡,殲滅揚子橋清軍。
太平軍繼續掃蕩東岸,陳家巷清營被陷,灣頭危急。慧成慌忙逃上船避難,「置軍務于不問」,他把一千余名兵勇調至灣頭、邵伯一線,以為自保。于是,清軍整個東路戰線徹底崩潰。
琦善在西岸坐視雷以諴、慧成先后敗逃,乘機疏劾東路清軍諸酋,企圖排除異己。咸豐只得將軍營諸頭目全行革職,各打五十板了事。
于是,揚州戰局急轉直下,賴漢英在曾立昌接應下,于12月26日從東城各門進入揚州。
琦善驚恐不安,擔心太平軍北趨清江、淮安,急忙派陳金綬扼邵伯,堵截北路交通線。但是,賴漢英并無北進意圖。楊秀清給他的任務是,迅速接出揚州守軍。
于是,當夜三更之后,賴、曾率將士「啟南門出走瓜州、儀征」,行走匆忙,首尾不能兼顧。西岸清軍主力由琦善督率渡河而東,適見太平軍撤軍,也不敢截擊。眼看賴漢英撤出輜重物資,棄守揚州后,清軍才敢「收復」空城。
之后,是一通捷報奏出,咸豐痛斥琦善無恥粉飾,旨稱:
「攻圍半載之賊,一旦竄出,成何事體,尚此鋪張,無恥已極。粉飾入奏,已屬有意掩飾,若被賊聞,豈不成一場笑話。」
相形之下,皇帝還知道顧全臉面。
其時,由于楊秀清分兵運動失誤,北伐軍連次告急,楊秀請無機動兵力可遣,只得挖肉補瘡,收縮天京戰區,撤出揚州將士,以曾立昌為統帥,組建北伐援軍,于1854年初北上。

這一決策導致太平天國江北領土的淪喪,只保留瓜洲一處江防要塞,與鎮江構成防侮犄角。江北大營坐取揚州后,立即移軍圍攻瓜洲,嚴防浦口、江浦、六合、儀征、揚州等江北軍事要地,對天京、鎮江間接施加軍事壓力。
因此,天京戰區的軍事態勢較前嚴峻。
(正文完)
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【關注】我私聊,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,第一時間回復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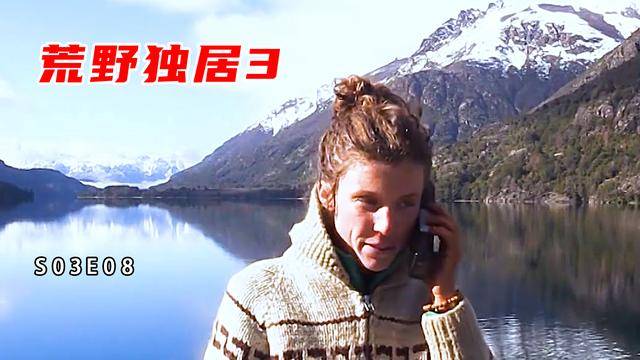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代表者: 土屋千冬
郵便番号:114-0001
住所:東京都北区東十条3丁目16番4号
資本金:2,000,000円
設立日:2023年03月07日
